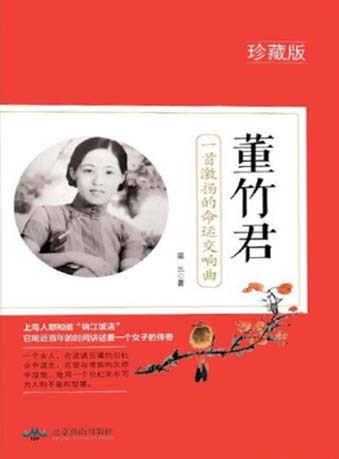董竹君:一首激扬的命运交响曲
一个旧上海滩洋车夫的女儿,12岁时沦为青楼卖唱女;14岁逃出火坑嫁与革命党人成为都督夫人,却不堪忍受封建大家庭和夫权统治,于29岁时毅然抛弃都督夫人的名头,选择离开;带着四个儿女两手空空回到上海打拼,历尽艰辛创办了上海锦江饭店。她的一生,开始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1900年,结束于香港回归祖国的1997年,经历了旧中国近代的政权更迭、战争饥荒多事年代,也经历了新中国的建立走向富国之路的时代,她的一个世纪,是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的缩影,更是一个女人不可多得的传奇。这本书,既是这个了不起的女人一生的缩写,也是她所生活时代的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