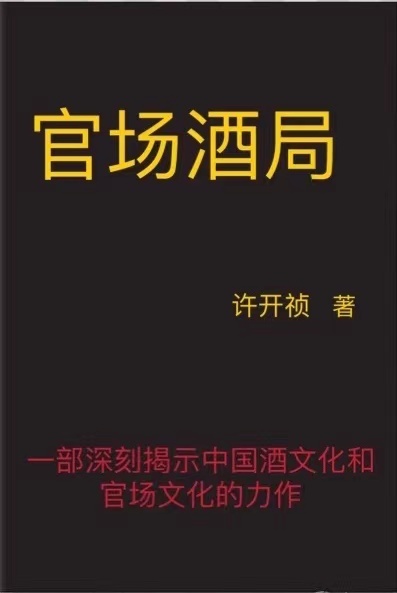官场酒局
官场酒局,以接待办主任田家耕的日常为背景,通过市里形形色色的酒局,展示了市长、副市长,各局长,以及县长,乡长等跑关系,跑门路,为自己或为县里谋利益的各种故事。故事看似热闹,但却悲怆沉重,因为每一场酒局,都是人生的一个投影。有人一醉方休,有人坐立不安。有人因酒而飞黄腾达,有人因酒而家破人亡。而田家耕,这个曾经县里的一把手,酒局的主宰者,却因一次意外而丢官,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又到市接待办担任主任,走所谓的曲线救国路线。曾经县里酒局的主宰者,成了市里酒局的服务者,他能适应得了这转变吗?在接待办主任位子上,他又是如何卧薪尝胆,深谋远划,为自己仕途的下一步做精心打算?市长关键,秘书长罗骏业等人,又怎样一个个在酒局上酒来酒去,看似喝掉的是酒,其实是官场中人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