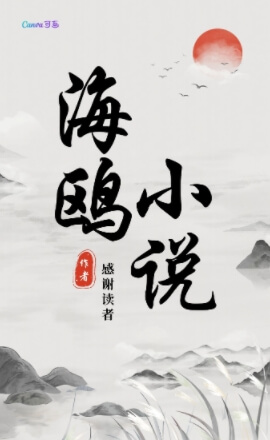我的前半生
注意我的前半生目前的最新章节为分节阅读75,我的前半生主要描写了第一章我的家世一醇贤亲王的一生一醇贤亲王的一生公元一九○六年,即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的旧历正月十四,我出生于北京的醇王府。我的祖父奕讠瞏,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初封郡王,后晋亲王,死后谥法“贤...
作家 爱新觉罗·溥仪
分類 现代言情 |
37萬字 |
7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