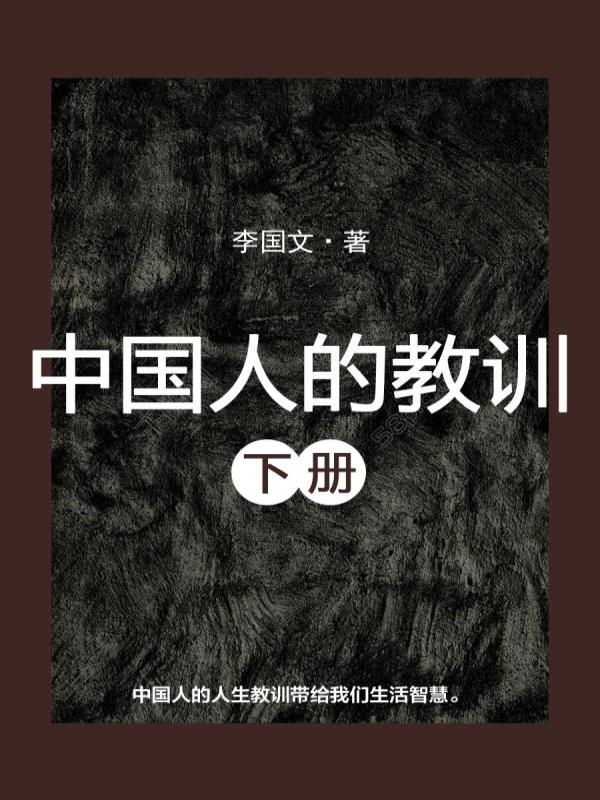中国人的教训.下册
本书是中国知名作家李国文专心于大众历史写作近三十年,在中国人血与火的往事中,找寻我们今天生活智慧的标志作。它以中国历代各类人物的生存状况、人生态度、命运遭际、成败得失为依托,突出了他们人生的一波三折、起落跌宕、苦心经营、艰难成功,是首部中国人反思人生轨迹、吸取生活经验的传记体通史。它让读者在借鉴古代中国人生存智慧的同时,更多地感悟今天每个人的活法。读史品人,以古知今,以史为鉴,为现实生活提供帮助。在这里读懂中国人生活的甘苦、读懂中国人薪火相传的方略、读懂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全面认知中国人的生活真谛、生存智慧、生命本质。本书立足大众的阅读习惯,内容深入浅出,结构波澜壮阔,情节催人泪下,语言幽默诙谐,阅读淋漓酣畅,是一部雅俗共赏极富睿智的畅销书。评论名家认为“这是当代将学识、性情和见解统一得最好的作品之一”。下册为宋元至清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