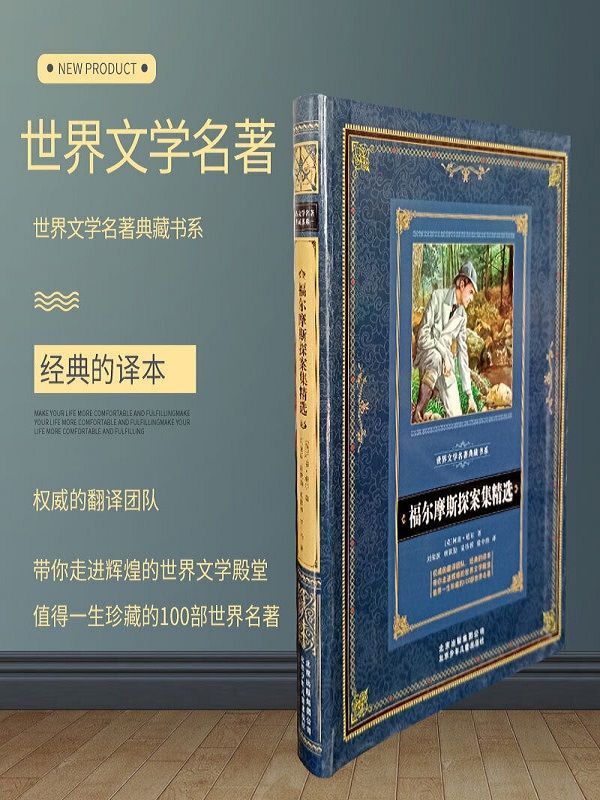福尔摩斯探案集精选
精心选取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之经典名篇,惊险的罪案现场、敏锐的案情剖析、抽丝剥茧的推理,帮助小读者培养细致的观察能力和缜密的思考能力。
作家 [英]柯南·道尔著 刘荣跃 唐跃勤等译
分類 出版小说 |
25萬字 |
46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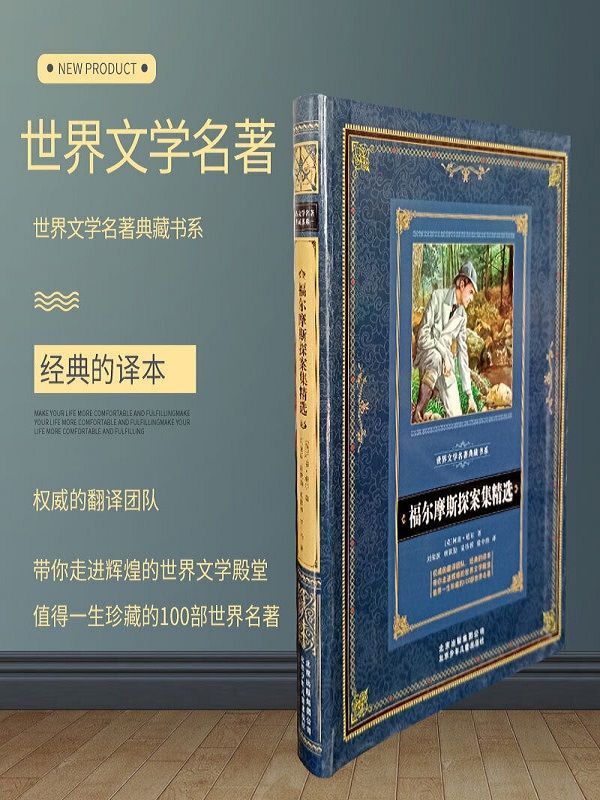
精心选取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之经典名篇,惊险的罪案现场、敏锐的案情剖析、抽丝剥茧的推理,帮助小读者培养细致的观察能力和缜密的思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