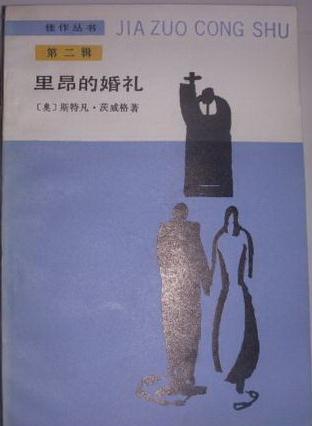里昂的婚礼
《里昂的婚礼》从法国大革命这—宏大的画卷中截取—个特殊的场景一一里昂大屠杀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小说中用十分简洁的文字描写了里昂城的腥风血雨。
作家 斯蒂芬·茨威格
分類 出版小说 |
1萬字 |
2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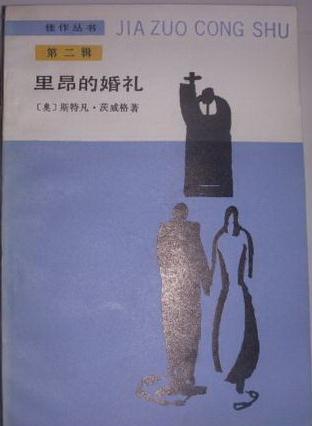
《里昂的婚礼》从法国大革命这—宏大的画卷中截取—个特殊的场景一一里昂大屠杀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小说中用十分简洁的文字描写了里昂城的腥风血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