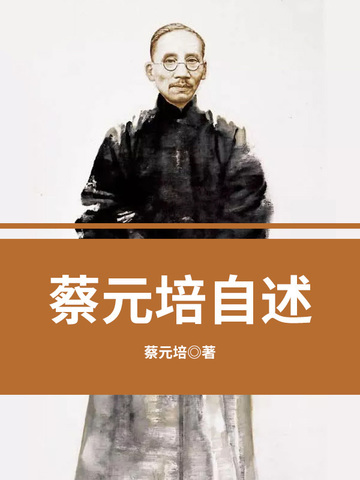蔡元培自述
《蔡元培自述》简介: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造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蔡元培自述》是蔡元培先生的自传以及自述性文章的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