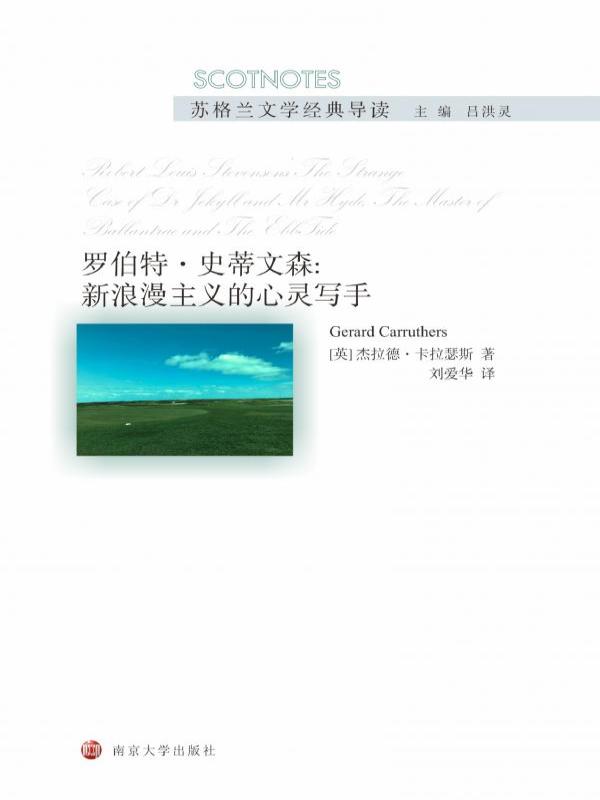罗伯特·史蒂文森:新浪漫主义的心灵写手
本书隶属于“苏格兰文学经典导读”丛书,本书的导读内容为我国读者熟悉的苏格兰小说家史蒂文森和以《化身博士》为代表的三部作品。本书从史蒂文森被当做儿童作家的误读现象入手,阐述他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对《化身博士》中的双重人格和人物塑造的社会文化性、《巴伦特雷的少爷》中的历史传奇与《落潮》中的背景设置情绪建构进行了重点阐释,并详细分析了三部小说的主题、人物塑造、叙事手法等,突出史蒂文森创作的艺术特征、苏格兰风格和文学价值。
作家 (英)杰拉德·卡拉瑟斯著
分類 出版小说 |
6萬字 |
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