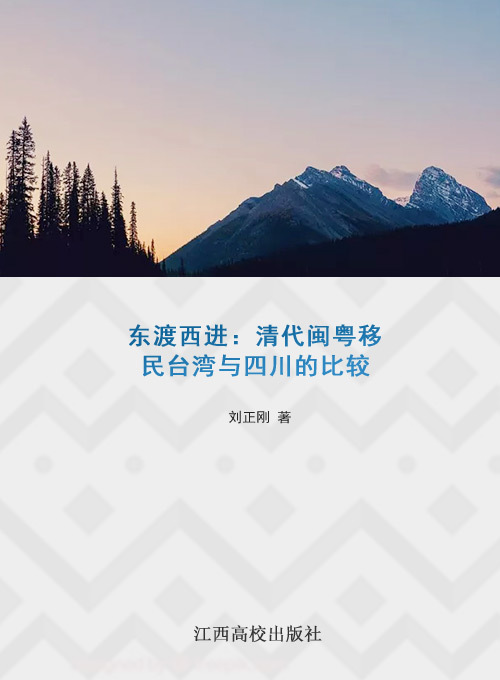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
《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是《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中的一册。本书是对清代闽粤移民海岛台湾与内陆四川的比较研究。移民建立的家族和地缘组织始终以祖籍地为蓝本,但构建的具体过程和功能则因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各具特色。两地移民均为官府指导下的经济趋利性流动,但台湾开发具有海洋型经济特征,四川则保持传统内陆型经济特征。随着移民的进入和定居,两地移民均经历了与土著的冲突、交流到融合的过程。两地移民社会的民间娱乐文化活动主要围绕中华传统神灵祭拜活动而开展,在凝聚乡情的同时,起到了教化作用。两地移民社会均出现了大量游民,成为两地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