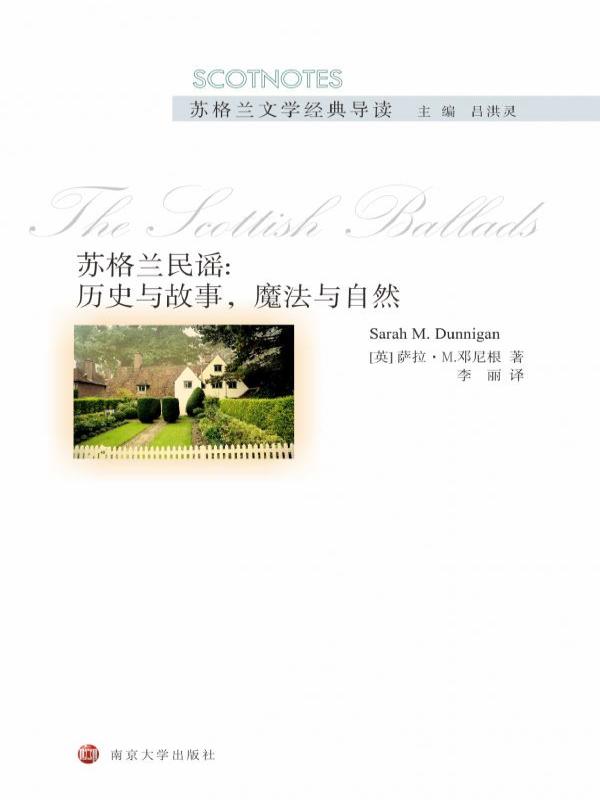苏格兰民谣:历史与故事,魔法与自然
本书对苏格兰文学的传统形式民谣进行了文笔简洁而内容丰富的介绍。本书从民谣的概念、音乐性、阅读体验、作者等基本方面谈起,介绍民谣的形式构成、历史性和戏剧性,展现民谣中的超自然元素,讲解民谣中的女性歌者与人物故事,促进人们了解诗韵悠扬民风盎然的苏格兰民谣。
作家 (英)萨拉·M.邓尼根著
分類 出版小说 |
9萬字 |
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