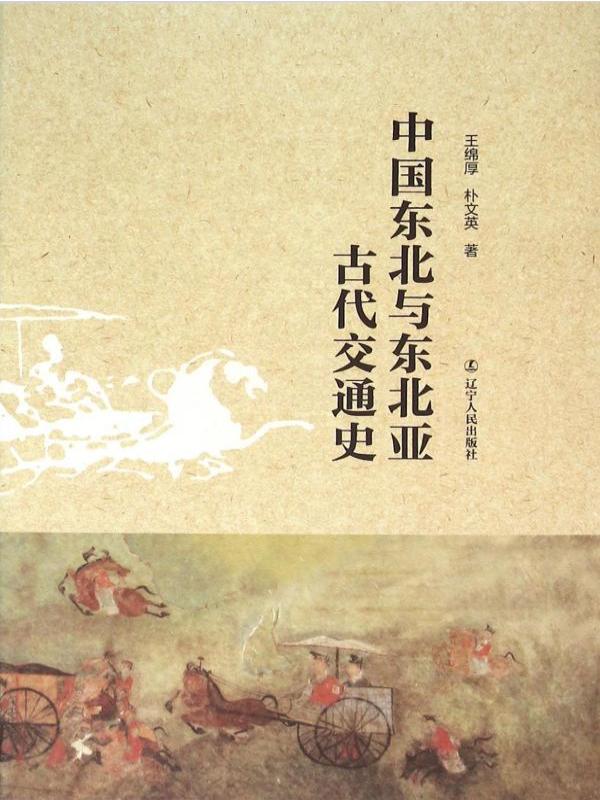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
《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是目前所见中国边疆史地专著中学术含量最高的一部著作。全书共60余万字,按时代顺序清晰详尽地论述了我国东北与东北亚地区,从上古至清王朝的海陆交通发轫、发展、繁荣的历时过程。
作家 王绵厚,朴文英著
分類 出版小说 |
45萬字 |
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