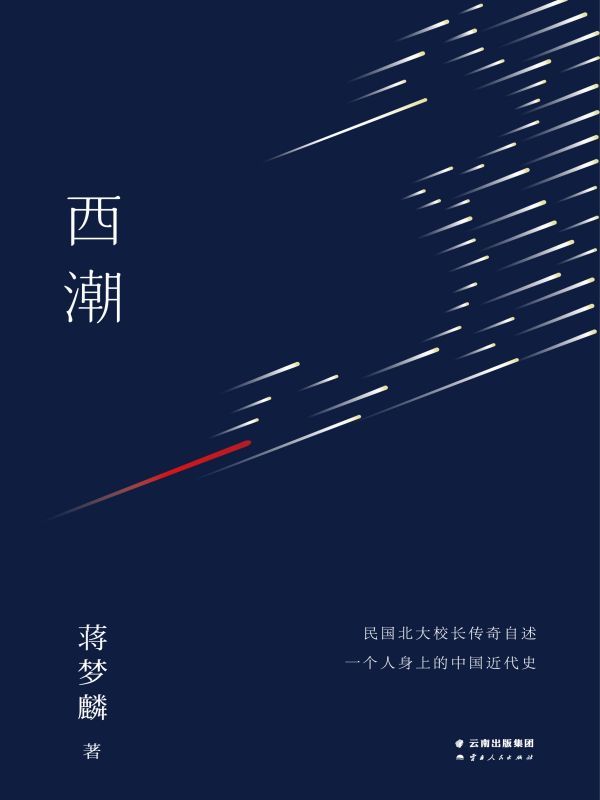西潮
在《西潮》的开篇章节中,作者蒋梦麟写道:“我所写下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不管它像什么,它记录了我心目中不可磨灭的景象,这些景象历历如绘地浮现在我的脑际,一如隔昨才发生的经历。在急遽递嬗的历史中,我自觉只是时代巨轮上一颗小轮齿而已。”童年生活、参加科举、留学美国、回国任职,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是怎么回事?民国初年的风云变幻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著名的西南联大有什么前世今生?蒋梦麟以学者的冷静、赤子的热情,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长达数十年的中国近代史。本书在五十年代初版后,引发惊人热潮,成为青年学生人手一册的“人生教科书”。《西潮》同时是哈佛大学远东研究所的指定参考书。